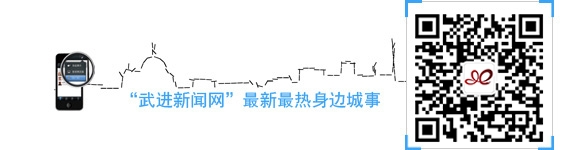гҖҖгҖҖеҘ¶еҘ¶еЁҳ家姓方пјҢеҚҒе…«д№қеІҒеҮәйҳҒеүҚжІЎжңүй—әеҗҚпјҢеҗҺз»ҸдәІжҲҡеҒҡеӘ’пјҢдёҖи§ҒеҖҫеҝғе«Ғз»ҷдәҶжҲ‘зҡ„зҲ·зҲ·жқҺеҺҡжҳҢгҖӮе©ҡеҗҺпјҢзҲ·зҲ·дёәе…¶еҸ–еҗҚ“зҺүзҗҙ”пјҢеңЁйӮЈдёӘе№ҙд»ЈпјҢиҝҷеҗҚеӯ—з®—жҳҜиҫғйӣ…иҮҙ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е№јж—¶“жҖ•е…Ҳз”ҹжүӢеҝғжү“жқҝеӯҗ”пјҢеҘ¶еҘ¶жІЎеҝөеӨҡд№…з§ҒеЎҫдҫҝејғеӯҰдәҶпјҢдҪҶиҝҷ并дёҚеҰЁзўҚеҘ№жӢҘжңүдёҖйў—“зҺІзҸ‘еҝғ”е’ҢдёҖеҸҢе·§жүӢгҖӮиЈҒиЎЈеҒҡеёҪгҖҒз»ҮжҜӣиЎЈгҖҒзәіеә•еҒҡйһӢпјҢеҸӘз»ҸеҘ№дёҖзңјпјҢж— еёҲиҮӘйҖҡпјҢжҲ‘们е§җеҰ№е…„ејҹе°Ҹж—¶еҖҷиә«дёҠзҡ„з©ҝжҲҙеҹәжң¬дёҠйғҪеҮәдәҺеҘ№жүӢпјҢеңЁз»ҸжөҺеӣ°йҡҫж—¶жңҹпјҢеҘ¶еҘ¶д№ҹжҳҜйқ дёҖеҸҢе·§жүӢдёәдәә家еҒҡиЎЈзү©жқҘиЎҘиҙҙ家用гҖӮ
гҖҖгҖҖдёҠдё–зәӘдёғе…«еҚҒе№ҙд»ЈпјҢзү©иҙЁз”ҹжҙ»иҝҳдёҚжҳҜеҫҲдё°еҜҢпјҢеҗғйЈҹд№ҹдёҚжҳҜеҫҲдё°еҜҢпјҢдҪҶз®Җз®ҖеҚ•еҚ•зҡ„йЈҹжқҗз»ҸеҘ№д№ӢжүӢпјҢжҖ»иғҪеҸҳеҮәи®ёеӨҡдёҺдј—дёҚеҗҢзҡ„иҠұж ·гҖӮеҘ№дјҡеҒҡжүӢж“ҖйқўгҖҒиҮӘеҸ‘й…өзҡ„й”…иҙҙйҰ’еӨҙгҖҒиҚ·еҸ¶еҸ‘зі•гҖҒеҚ—з“ңйҰ…йҘјзӯүпјҢе…¶дёӯеҚ—з“ңйҰ…йҘјеҗҺжқҘдј жүҝз»ҷдәҶеӨ§еҰҲеҰҲ(еӨ§дјҜжҜҚ)е’ҢжҲ‘зҡ„еҰҲеҰҲпјҢжҲҗдәҶиҖҒжқҺ家зҡ„дј е®¶жүӢиүәгҖӮеҘ¶еҘ¶еҢ…зҡ„“е°Ҹи„ҡзІҪ”еӨ§е°ҸеқҮеҢҖгҖҒеӨ–иЎЁе…үжҙҒгҖҒзіҜзұізҙ§е®һ(иҝҷдёӘжҲ‘еҰҲеҰҲд№ҹеӯҰеҲ°жүӢдәҶ)пјҢе°Ҹж—¶еҖҷжңҖзҲұеҗғеҘ¶еҘ¶еҢ…зҡ„иөӨиұҶзІҪе’ҢиҠұз”ҹзІҪпјҢеҶ·зІҪеӯҗиҳёзҷҪз Ӯзі–пјҢдёҖеҸЈе’¬дёӢеҺ»д»ҺиҲҢе°–еҲ°иғғйҮҢйғҪжҳҜеҰҘеҰҘзҡ„дә«еҸ—гҖӮеҘ¶еҘ¶и…ҢеҲ¶зҡ„зі–йҶӢеӨ§и’ңеӨҙй…ёз”ңйҖӮдёӯгҖҒжё…и„ҶеҸҜеҸЈпјҢд»Өдәәйҡҫеҝҳ(иҝҷдёӘзҲёзҲёз»§жүҝдәҶпјҢеҸӘжҳҜж„ҹи§үе‘ійҒ“иҝҳжҳҜз•ҘйҖҠдёҖеұӮ)гҖӮеҘ¶еҘ¶и…Ңзҡ„е’ёйёӯиӣӢд№ҹжҖ»жҳҜе’ёеәҰйҖӮдёӯиҝҳ“еҮәжІ№”пјҢдёҚеғҸзҺ°еңЁи¶…еёӮйҮҢд№°зҡ„иҰҒдёҚжңӘе…Ҙе‘ігҖҒиҰҒдёҚе°ұжҳҜиҷҪжІ№жұӘжұӘдҪҶ“жӯ»йҪҒ”е’ёгҖӮ
гҖҖгҖҖи®°еҝҶдёӯпјҢеҘ¶еҘ¶иҝҳдјҡзј–зҜ®еӯҗпјҢеҸӘжҳҜз”Ёзҡ„дёҚжҳҜз«№зҜҫпјҢжҳҜйӮЈз§ҚеҢ…зқҖеЎ‘ж–ҷдә”йўңе…ӯиүІзҡ„з»Ҷй“…дёқгҖӮи®°еҫ—еҘ№жӣҫз»Ҹзј–иҝҮдёҖдёӘеёҰзӣ–еӯҗзҡ„зҜ®еӯҗпјҢжңүдёҖж¬ЎдёҖеҸӘйә»йӣҖиҜҜйЈһиҝӣдәҶеҺЁжҲҝпјҢдёҖеӨҙж’һзҺ»з’ғдёҠи·ҢиҗҪеңЁең°пјҢеҘ¶еҘ¶дҫҝжҚүдәҶе®ғе…іеңЁиҝҷеҸӘзҜ®еӯҗйҮҢпјҢжҢӮеңЁеҺЁжҲҝзҡ„еўҷдёҠпјҢи®©ж”ҫеӯҰеӣһжқҘзҡ„жҲ‘е’Ңејҹејҹж¬Је–ңдәҶеҘҪдёҖйҳөеӯҗгҖӮ
гҖҖгҖҖдёҚз®ЎжҳҜеңЁеҜҢи¶ізҡ„еЁҳ家пјҢиҝҳжҳҜеҮәе«ҒеҗҺз»ҸеҺҶдәҶз§Қз§ҚеҸҳж•…пјҢе“ӘжҖ•жҳҜ1954е№ҙеұ…дҪҸзҡ„й•Үжұҹе°Ҹз ҒеӨҙйҒӯй•ҝжұҹж°ҙзҒҫпјҢеҘ¶еҘ¶жӢ–зқҖдёӨдёӘиҖҒдәәгҖҒдёүдёӘе№ҙе№јзҡ„еӯ©еӯҗеӣһеҲ°жү¬е·һеЁҳ家еҖҹдҪҸдәә家зҡ„иҢ…еұӢж—¶пјҢеңЁеҘ№зҡ„ж–ҷзҗҶдёӢпјҢдёҖ家дәәиө°еҮәжқҘж°ёиҝңжҳҜжё…жё…зҲҪзҲҪгҖҒеҲ©еҲ©зҙўзҙўзҡ„пјҢеҚідҪҝиЎЈиЎ«йҷҲж—§дҪҶд»ҺжңӘз ҙиЎЈзғӮиЎ«иҝҮпјҢжү“дёӘиЎҘдёҒд№ҹжҳҜжңүжЁЎжңүж ·зҡ„гҖӮ
гҖҖгҖҖеҘ¶еҘ¶20еӨҡеІҒејҖе§ӢеӯӨиә«жҢҒ家(зҲ·зҲ·еЁ¶дәҶеӨ–е®Ө并且еҲ°дёҠжө·е®ү家)пјҢдёәжҺ’и§ЈеҝғдёӯиӢҰй—·пјҢеҗёдёҠдәҶзәёзғҹпјҢдҪҶи®°еҝҶдёӯеҘ№зҡ„зүҷйҪҝдёҖзӣҙзҷҪзҷҪзҡ„пјҢиә«дёҠд№ҹжІЎжңүд»»дҪ•йҡҫй—»зҡ„зғҹе‘іпјҢдёҖеӨҙзҹӯеҸ‘ж•ҙж•ҙйҪҗйҪҗеҲ«еңЁиҖіеҗҺпјҢдёҫжүӢжҠ•и¶ідёҚеӨұеӨ§е®¶й—әз§Җзҡ„з«Ҝеә„еҫ—дҪ“гҖӮ
гҖҖгҖҖд»Һе°ҸпјҢеҘ¶еҘ¶дҫҝж•ҷеҜјжҲ‘们“еқҗиҰҒжңүеқҗзӣёгҖҒз«ҷиҰҒжңүз«ҷзӣё”“еҗғйҘӯдёҚиҰҒе’Ӯе·ҙеҳҙ”“еӨ§дәәжІЎдёҠжЎҢе°Ҹеӯ©еӯҗдёҚеҘҪе…ҲеҠЁзӯ·”“еҒҡдәәиҰҒжңү规зҹ©”гҖӮеңЁеҫ…дәәеӨ„дё–дёҠпјҢеҘ№дёҖзӣҙж•ҷеҜјжҲ‘们иҰҒиҮӘе°ҠиҮӘзҲұпјҢе®ҒеҸҜиҮӘе·ұиҫӣиӢҰдәӣпјҢе°ҪйҮҸе°‘з»ҷеҲ«дәәжүҫйә»зғҰгҖӮ
гҖҖгҖҖеҗ¬е§‘姑иҜҙпјҢеҘ¶еҘ¶еҺ»дё–йӮЈеӨ©пјҢеҘ№жғізқҖзҡ„д№ҹжҳҜдёҚиҰҒйә»зғҰеҲ«дәәпјҢжҲ–и®ёжҳҜзҹҘйҒ“иҮӘе·ұеӨ§йҷҗе°ҶиҮіпјҢдҫҝ让姑姑帮еҘ№ж—©ж—©ж“Ұжҙ—иә«дҪ“гҖҒжҚўеҘҪеҜҝиЎЈпјҢдёҖеҲҮеҒңеҪ“еҗҺдҫҝе®ү然зҰ»дё–дәҶгҖӮ
гҖҖгҖҖеҘ¶еҘ¶еҝғең°е–„иүҜ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ңЁзҲ·зҲ·еҸҰз«Ӣ家е®ӨгҖҒ家еўғиөӨиҙ«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Ҙ№дҫқ然еҜ№зҲ·зҲ·зҡ„еҰҲеҰҲе’ҢиҲ…иҲ…дёҚзҰ»дёҚејғпјҢ并且дёәдёӨдёӘиҖҒдәәе…»иҖҒйҖҒз»ҲгҖӮ家йҮҢз©·еҫ—жҸӯдёҚејҖй”…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зңӢи§ҒжңүиҰҒйҘӯзҡ„дёҠй—ЁпјҢеҘ№жңүдёҖдёӘиҸңзі еӣўеӯҗд№ҹиҰҒеҲҶеҚҠдёӘз»ҷдәә家гҖӮйӮЈдёҖе№ҙпјҢеҫ—зҹҘдёҠжө·зҡ„е°Ҹ姑姑10еӨҡеІҒдёӢж”ҫеҲ°е®үеҫҪеӨ©й•ҝеҺҝеҶңжқ‘пјҢж’’еҶңиҚҜж—¶дјӨдәҶзңјзқӣпјҢеҘ№йҡ”дёүеІ”дә”йҖҒиЎЈйҖҒйЈҹпјҢеҗҺжқҘе№Іи„ҶжҺҘеӣһ家дёӯеҘҪз”ҹз…§ж–ҷгҖӮе°Ҹ姑姑еҗҺжқҘдёҠдәҶеёҲиҢғеӯҰж ЎпјҢеӣһеҲ°дёҠжө·еҪ“иҖҒеёҲгҖҒе°ҸеӯҰж Ўй•ҝпјҢиҜҙиө·еҘ¶еҘ¶пјҢеҘ№д№ҹжҳҜжӯўдёҚдҪҸзҡ„ж»Ўи…”ж„ҹжҝҖгҖӮ
гҖҖгҖҖе·ҰйӮ»еҸіиҲҚжІЎжңүдәәдёҚеӨёиөһеҘ№зҡ„д»ҒзҲұгҖӮи®°еҝҶдёӯпјҢ家дёӯдҪҶеҮЎеҒҡзӮ№еҘҪеҗғзҡ„пјҢеҘ¶еҘ¶жҖ»дјҡйҖҒйӮ»еұ…家дёҖд»Ҫ;иӢҘжҳҜйӮ»еұ…йҖҒдәҶдёңиҘҝжқҘпјҢеҘ¶еҘ¶жҖ»жҳҜдјҡжҠҠзӣӣдёңиҘҝзҡ„зҜ®еӯҗжҲ–зҜ“еӯҗж“Ұжҙ—е№ІеҮҖпјҢ然еҗҺеҶҚж”ҫзӮ№дёңиҘҝ“еӣһдёӘжғ…”пјҢеҘ№зҡ„еҸЈеӨҙзҰ…дҫҝжҳҜпјҡ“дәә家еҘҪеҝғжғізқҖжҲ‘们пјҢжҲ‘们дёҚеҘҪдәҸеҫ…дәә家гҖӮ”
гҖҖгҖҖеңЁзҹҝдёҠдҪҸ家еұһеҢә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дҪҸйҡ”еЈҒзҡ„еҲҳдјҜдјҜеӯ©еӯҗеӨҡпјҢдәҢдё«еӨҙеҫ—дәҶе°Ҹе„ҝйә»з—№з—ҮпјҢиҖҒе©ҶеҸҲеёёе№ҙз”ҹз—…пјҢеҘ¶еҘ¶зңӢеңЁзңјйҮҢгҖҒеҝ§еңЁеҝғдёӯпјҢз”ҹжҙ»дёҠжҖ»жҳҜдјҡдёҚеЈ°дёҚе“Қең°жҗӯжҠҠжүӢгҖӮжңүдёҖеӣһзңӢи§ҒеҲҳдјҜдјҜзҡ„йһӢеӯҗз ҙдәҶи®ёд№…пјҢз©ҝеңЁи„ҡдёҠд№ҹжІЎдәәж–ҷзҗҶпјҢдҫҝжҠҪз©әз”ЁзўҺеёғжҠ№дәҶжөҶгҖҒеҜҶеҜҶең°зәідәҶеә•пјҢз»ҷд»–еҒҡдәҶеҸҢй»‘иүІеёғйһӢгҖӮеӨ§й«ҳдёӘзҡ„еҲҳдјҜдјҜжӢҝеҲ°йһӢйЎҝж—¶зғӯжіӘзӣҲзң¶пјҢжү§ж„ҸиҰҒи®ӨеҘ¶еҘ¶еҒҡе№ІеЁҳгҖӮжҲ‘们дёӨ家дәәзҡ„еҸӢи°ҠдёҖзӣҙеҲ°еҘ¶еҘ¶еҺ»дё–еҗҺд№ҹжІЎжңүж–ӯиҝҮгҖӮ
гҖҖгҖҖ“жңӘз»Ҹи®ёеҸҜ дёҘзҰҒиҪ¬иҪҪ”
иҝҪеҝҶжҲ‘зҡ„еҘ¶еҘ¶ж–№зҺүзҗҙ
иҙЈзј–пјҡ еӯҷе©·е©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