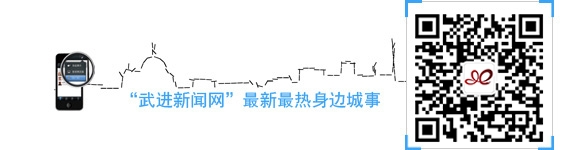从来没有想过,会在一场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”的常州午后时间,突发奇想,选择了一屁股坐在游船上,幻想像年轻时的赵元任、周有光、瞿秋白那样,或仰视,或俯视,或环视,将眼前青果巷错落有致的屋宇、静水深流的一湾清幽,尽收入“远行者”彀中。此时此刻,我是这条小河上唯一佯装远行的漂泊者。
遥想那时的出行,心中就出现了“南船北马”的所谓常识。这里的南船,应是乌篷船吧。周作人在《乌篷船》里这样介绍它:“篷是半圆形的,用竹片编成,中央竹箬,上涂黑油;在两扇‘定篷’之间放着一扇遮阳,也是半圆的,木作格子,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,径约一寸,颇有点透明,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。”
我乘坐的船不是如此简陋,不,如此古老的乌篷船,而是通体用红油漆粉刷过的机械船。船头并没有竹篙,却有一张竹凳,怕水的人可以安坐;若是不怕水,不晕船,可在船头的木板上迎风而立,视野开阔。无边的丝雨恰如愁绪,煽动着幽幽的清梦。要是撑起一把江南巧手编织的油纸伞,瞬间便幻化成《聊斋》里多情的狐仙,或者水灵灵的惆怅女子。可惜自己只是一介苍颜白发的须眉浊物,会不会不慎污了一池碧水?皱了一方靛青?
船舱内可坐,亦可立,船体两侧设置红漆长凳。“中间可放一顶宽大方桌,四个人坐着打马将——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吧?”这也是《乌篷船》里的句子。我一个人乘坐,麻将呢?不熟,不会,不打也罢。既然是佯装远游,还是做一个安静的游子吧。
“船尾用橹,大抵两支,船首有竹篙,用以定船。船头着眉目,状如老虎,但似在微笑,颇滑稽而不可怕。”这只是周作人时代的陈设,我的船尾,坐着船娘。她摇动机械舵手,轰隆隆一阵轻响,河水便在船舱两边和尾部荡漾,似乎触动了水底摇摇的青荇,也重启了心中珍藏的《再别康桥》。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,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。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。”船舱内的音响,传来悠悠戏腔。我问她:“这是昆曲《牡丹亭》第十出《惊梦》吧?”
“对对对!”她有些欢喜。沉默一旦被打破,她开始滔滔不绝介绍青果巷的历史掌故,刘国钧、唐荆川、赵翼、黄仲则、盛宣怀……她所叙述的,有些我早烂熟于心,有些我似醍醐灌顶。杏花烟雨江南,大概率都有这样的流水、小桥、故事、传说。
游船的时间是短暂的,从开始到结束,只有20分钟,我却似做了一场清梦,能否胜过几度人生秋凉?我突然想起了苏东坡,他来过青果巷吗?河两边的住户,有没有过站在自家小码头上,翘首盼望着他家来,喝上一杯封缸酒,吃上一尾河豚鱼,品鉴一壶金坛雀舌,说上一句“此地甚好,便是吾家”的川音。
苏轼离开了,但青果巷仍在,千年以后还在。“我”来了,无数次来了,今后还会来。走马青石板上,让马蹄嘚嘚;也许轻摇橹柄,让欸乃声声。或者钻进随便一家店铺,找一个临河的窗,品茗把酒,焚一炷香,读一本书,写一首诗,装模作样,和这里的先人们对对话,不说柴米油盐,不说糖酱醋烟,只话面朝大海,更谈春暖花开。
“未经许可 严禁转载”
船走青果巷
责编: 孙婷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