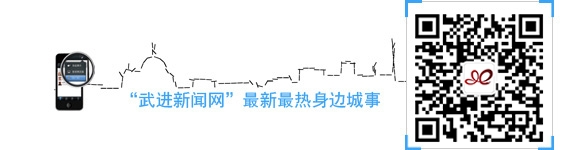决定去一趟西湖的时候,居然纠结了一下:是带张宗子的《陶庵梦忆》还是《夜航船》?一直以来,我都认为《夜航船》是书生之书、学问之书,如果不是为了钻研,可以不看的;而《陶庵梦忆》是才子之书、孤愤之书,如果不是为了钻研,一定要看的。
还是做一道选择题吧,带《陶庵梦忆》出发。
高铁从常州北站开出,经过一条V字形的路线,停靠在杭州东站。细雨飘洒了一个夜晚,江南的天空阴郁满面,大地湿漉漉的,似乎有意营造一种伤感的氛围。毕竟,断桥、岳王坟、苏小小墓、小孤山、灵隐寺什么的,对于我来说,凭吊的意味,显然大于游玩,这一切,都是张岱惹的祸。
那就先说说他的《湖心亭看雪》吧!极好的文字,极好的西湖,极好的痴,极好的三大白,极好的毳衣炉火,极好的雾凇沆砀,极好的天与云与山与水,极好的上下一白,极好的湖上影子,极好的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,极好的孤独。
张岱是崇祯五年十二月来的西湖。那年按照西历,是1632年,大明朝还有12年寿命。那次大雪纷飞,居然下了三天,张打油的诗正是极妙的解注:“江上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西湖上人鸟声俱绝,也是给张岱的更定行船做铺垫,正如此时落向大地的蒙蒙细雨为我铺垫一样。
《陶庵梦忆》里有一句名言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我以为,“癖”和“疵”,是说痴人必定有深情和真气,才可以与之交往。张岱本人就是有深情和真气之人。你看他选择的出行条件:大雪,人鸟声俱绝,更定,小舟独往,还有和他一样“痴”的金陵人,当然,还有祭祀故国的三大白,还有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悲悯、孤独和遗世孑立的哲学之思。
我去的西湖,并没有大雪三日,仅仅是乌云翻墨未遮山,水面初平云脚低。游人和游人近距离接触,即使站着不动,也会不由自主往前。
而张岱在《西湖七月半》里明示过,看西湖,最好的时间,不是“楼船箫鼓,峨冠盛筵,灯火优傒,声光相乱”;不是“亦船亦楼,名娃闺秀,携及童娈,笑啼杂之”;不是“亦船亦声歌,名妓闲僧,浅斟低唱,弱管轻丝,竹肉相发”,而是“岸上人亦逐队赶门,渐稀渐薄,顷刻散尽矣”。此时:“吾辈始舣舟近岸。断桥石磴始凉,席其上,呼客纵饮……向之浅斟低唱者出,匿影树下者亦出。吾辈往通声气,拉与同坐……月色苍凉,东方将白,客方散去。吾辈纵舟,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,香气拍人,清梦甚惬。”
这个闲适情状,民国时朱自清也留下相似的文字:“那晚月色真好,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。本来前一晚是‘月当头’;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。那时九点多了,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。有点风,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;当间那一溜儿反光,像新砑的银子。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。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……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;是阿弥陀佛生日,那边蛮热闹的……到了寺里,殿上灯烛辉煌,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,好像醒了一场梦。”
两人在文章里都写到了月夜,一个在十一月,一个在七月半。不同的是,一个似冷却热,一个似热却冷。而此时的我呢?裹挟在一众人的“热”气里,观着一池春分时的清水,虽然不能和他们一样,却也好像醒了一场梦。这梦,是从纸张里走出来的,也就得留在文字里。
再见,西湖;再见,张宗子。下次来,我选择月色撩人夜。
“未经许可 严禁转载”
在西湖,想起张宗子
责编: 孙婷婷